宋朝 北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
Posted 宰相
篇首语:时间铭记梦想的足迹,历史镌刻奋斗的功勋。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宋朝 北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朝 北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
英宗赵曙皇后高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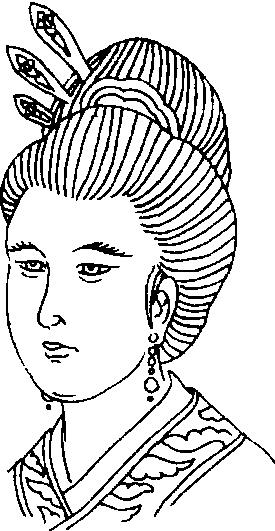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刚刚病死,北宋政坛上就卷起一阵摧新复旧的狂飙: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赵顼和王安石等人主持实施达16年之久的新法,被全盘否定,逐个废除; 太祖、太宗以来确立的所谓祖宗之法则僵尸还魂,全面恢复; 原先因参与或支持变法而获不次升擢的新进之士,相继被这股狂飙吹落乌纱,贬窜江湖; 起先因反对或破坏变法而遭排挤打击的元老旧臣则纷纷趁势东山再起,荣归庙堂。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掀起这阵狂飙的便是赵顼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
高氏,乳名滔滔,祖籍亳州蒙城(今属安徽),出身门第和她的姓氏一样异常高贵。她的曾祖是太宗时就以武功起家官封忠武军节度使的高琼,她的祖父高继勋也有功于王室,官至节度使,父亲高遵甫任北作坊使,母亲乃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母亲的胞妹就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曹皇后非常疼爱这个小外甥女,把她接进宫廷,养在自己身边。可巧,仁宗赵祯因没有儿子,也把4岁的侄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养到宫里。滔滔与宗实同年出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嬉闹玩耍,形影不离,亲热得象同胞兄妹一样,宫中上下都习惯地将宗实称为官家儿,滔滔为皇后女。赵祯每逢瞧见他俩耳鬓厮磨的热乎劲儿,非常开心,经常逗弄宗实说: “娶皇后之女当媳妇如何?”宗实和滔滔在宫中生活了五六年。宝元二年(1039)八月,赵祯的第二个儿子赵听出生,宗实和滔滔便各自回到父母家中。转眼春秋10载,滔滔年已及笄,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黄花姑娘。按当时的礼俗可以待字而嫁了。赵祯想起昔日的情景,有天对曹皇后说: “咱夫妇老而无子,过去收养的十三(赵宗实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滔滔,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为十三、你为滔滔主婚,让他俩两相嫁娶吧。”庆历七年(1047)初,高氏嫁到濮王府,封为京兆郡君,当时宫中称此事为“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 ,传为佳话。小两口新婚燕尔,如胶似漆,和睦缱绻,感情比孩童时更加亲密。次年四月,便收获了第一个爱情的果实,取名赵仲鍼,后改名赵顼。以后的十几年间,高氏更是硕果累累,到赵曙登基时,她已是4个儿子(颍王赵顼、歧王赵颢、润王赵颜、嘉王赵頵)和一个女儿(封寿康公主)的高堂老母了。
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赵曙当上了皇帝,二十五日,高氏正位中宫,成了皇后。4年后,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她又成了太后。从高氏一生的作为来看,在对待个人名利和高家的地位待遇等问题上,她很具有一些谦虚的美德。这方面与真宗那位章献明肃刘皇后总是处心积虑地抬高娘家人的地位的做法不太一样,而与婆婆曹皇后颇为相似。
高氏立为皇后之前,她的弟弟高士林已在宫中担任内殿崇班了。士林做的虽是武官,但对儒学很是喜爱,广泛涉猎经史,能通大义,尤有巧智。赵曙见他是个人才,又是内弟,在内殿崇班的职位上也干了不少时间了,便多次想提拔他,可是每次与高氏说起,高氏都不同意,还说: “士林得以为官禁从,这已经是很过分了,咱们岂能与先朝的皇后们攀比呢?”在她的阻拦下,直至治平三年(1066),高士林死后,赵曙才追赠他为德州刺史。有年元霄节,高氏登上宣德楼观赏彩灯,外戚们也全被召集到楼前,赵顼几次派人向她禀报: “应该向外戚们推恩赏赐,如何办法,请太后降旨。”高氏回答: “我自会处之。” 第二天,赵顼问: “怎样处之?” 高氏说: “年纪大的各赐一匹绢,小的分给乳糖狮子两个。”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份少得可怜的赏赐。赵顼即位后,多次想为高氏营造一处大的宅第,高氏仍然不许,过了很久,才勉强同意赵顼把望春门外的一块空地赐给高家作宅基。按规定,太后家营造新居的所有花费,都是可以从大农寺公款中支取的,但高氏却坚持只使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私房钱,自始至终没有动用过大农寺一文钱。
高氏与曹皇后相似之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政治观点上,两人更是惊人的一致,而且高氏比曹皇后更为保守。她对祖宗之法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任何变法革新的事都觉着扎眼。当上太后之后,经常和他来往的,除了宦官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贵戚、宦官及一部分朝臣组成的旧党,围绕市易法、免役法与新党掀起第二次变法斗争浪潮的时候,高氏便和曹皇后一起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抹眼淌泪地劝说赵顼不要轻易变革祖宗法度,要求把王安石赶出朝廷。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从这时开始,高氏就实际扮演起了旧党的天然领袖的角色。旧党分子在变法过程中或因失败被逐出朝廷,或被迫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他们丝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以便卷土重来。机会果然被他们等到了,这便是赵顼死后,因继位的宋哲宗年幼,而由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新政局。
元丰七年(1084)冬,赵顼生病,翌年正月过后,越发沉重,后来话都说不清楚了。还在疾病初起之时,赵顼就有了立太子的打算,准备在来年春天,把长子延安郡王赵佣出阁立为太子,并延请司马光、吕公著做赵佣的师傅。眼看赵顼的病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高氏、皇后向氏,以及左相(首相)王珪等人对赵顼的安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高氏考虑得还非常周到,为了让赵佣仓促即位时能有一套可身的御袍,她暗中对宦官梁惟简说: “你回家一趟,找人赶制一袭10岁小儿穿戴的黄袍,秘密带给我。” 可是右相(副相)蔡確及其亲信职方员外郎邢恕却有另外的打算。蔡確早年靠依附王安石起家,后见王安石失势,便公开抨击王的过失,邢恕也是个趋炎附势、善搞阴谋的投机分子。两人不了解高氏在立太子问题上的真正意向,以为高氏会像史书上记载的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一样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蔡確还担心赵顼重新起用吕公著、司马光会取代他为宰相,便阴谋把歧王赵颢或嘉王赵頵推上台,讨好高太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蔡確授意下,邢恕找到高氏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说: “我家有棵桃树开了白花,据 《道藏》记载白桃花能治好皇上的病,请二位一起去看看吧。” 两人随他回家,见桃树上盛开的分明是粉嫩的红花,吃惊地问: “白桃花在哪?” 邢恕干笑几声,拉着两人的手说: “蔡丞相让我向二人说句心里话,皇上看来快不行了,延安郡王只是个小孩,太子之事应有定论,歧、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 两人更加惊讶,“这是什么话!君难道想贻祸我家吗?” 慌忙跑了出去。邢恕碰了钉子,但也摸清了高氏的真实意图,就和蔡確回过头来准备首先拥立赵佣,夺得定策之功,同时借机除掉和蔡確有矛盾的王珪。
二月底,宰执大臣前往福宁殿问疾,起初没敢提及建储之事,退下后,都到了枢密院的南厅议论此事。蔡確一个劲地逼王珪表态,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杀手将王珪诛死。王珪一向谨慎怕事,是个出名的 “三旨” 宰相(他上殿奏事,称 “取圣旨” ,皇上可否之后他说 “领圣旨” ,退而传达就说 “已得圣旨” ),又口吃得很,蔡確一再追问,他结结巴巴连说几个是字,才期期艾艾地说: “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 蔡確又是干瞪眼无计可施了。宰执大臣再次来到赵顼病榻前,王珪说: “去冬曾奉圣旨,道是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请求早日立为太子。” 连说了3遍,赵顼才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请求,太后权同听政,赵顼也微微点了点头。众人退出时,恰好在殿前遇见了赵颢和赵頵,参知政事章惇厉声说: “已得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怎么样?” 赵颢说: “天下大幸。” 就这样在表面平静的气氛中把后事安排妥了,蔡確、邢恕的阴谋,高氏一直不知道。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氏垂帘坐在一边,赵佣站在帘外,高氏说: “相公们立的这个孩儿很好。清俊好学,已能背诵7卷《论语》 了,平时不贪玩,只是学书。并且非常孝顺,自官家服药,从未离开过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 说罢从帘内递出两本 《延寿经》和 《消灾经》 ,王珪叩拜称贺。接着就到前廷宣读了起草好的制词: 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备礼册命。同时公布诏命: 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

赵顼没有熬到康复那一天,三月五日,在福宁殿与世长辞。当天,赵煦即位于柩前,穿的就是高氏为他秘密制作的那套黄袍。这年高氏54岁,而赵煦刚刚10岁。
老来丧子的悲痛,丝毫没有降低高氏保守的政治热情。还在赵顼弥留之际,她就当着赵顼的面说: “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共20余条。”她对新法憎恨到这等地步,竟连垂死的儿子都不肯原谅。现在年幼的孙子当皇帝,她不仅被尊为太皇太后,而且继续权同听政,实际掌握了最高决策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场彻底清算新法的运动便毫无顾忌地展开了。由于高氏操纵的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所以史书上称之为 “元祐更化” 。
垂帘听政不久,高氏就为全面废除新法,做起了舆论上的准备。元丰八年五月五日,在朝堂贴出诏令,让百官言朝政阙失。但这时仍然在朝廷各要害部门掌权的新党人物,却不愿意反对派的言论趁此机会冒出头来,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诏令中做了6条规定加以限制。说上书言朝政阙失是可以的,但若怀有阴谋,或者言事的内容超过了本职范围,或者造谣生事,干扰机务,或者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求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猎取虚名,如此者,必罚无赦。紧接着,太府少卿宋彭年和水部员外郎王锷就被扣上“非职而言”的帽子罚铜30斤。新党的抵制,使高氏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人势力的强大和自己在朝廷中的孤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迫切需要得到旧党干将们的支持,迫切需要把原先遭受排挤的旧党人物重新拉回到朝廷中来。因此,在贴出求谏诏令的同时,她就派出驿车接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元老旧臣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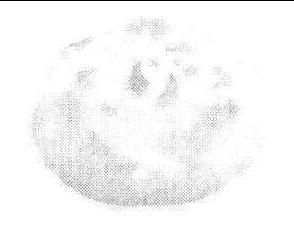
司马光,字君实,出身于陕西望族。传统的封建礼仪和渊博的学问,以及不大争夺官职和较其他士大夫为朴素的日常生活——司马光的这些个人特点,使他成为闻名朝野的人物。苏轼在一首诗中写的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就是对司马光之饱享盛名的真实渲染。然而,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知名却不来源他的政治才干,而是来源于他对新法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对于他的政治才能,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有一个相同的估价,韩琦称司马光 “才偏规模浅” ; 大理学家程颐也说司马光如同人参、甘草,在疾病不重时还可使用,一旦病情严重就不中用了; 至于变法派中的章惇则直斥之为乡巴佬、村夫子。但由于司马光从变法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每逢一项新法出台,他都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大唱反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这使他赫然成了反对派阵营中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一面纠集旧党的旗帜,而当之无愧地受到了旧党们的一致推崇和高氏的极度垂青。三月十七日,司马光从洛阳来汴京为赵顼奔丧,然后依旧回到洛阳,高氏听说他已经走了,懊悔得不得了,随即派内供奉官梁惟简赶往洛阳劳问,称赞他历事数朝,忠亮显著,要他进言政务得失,并询问治国应先从何处人手。不多久,又派专车接司马光进京。司马光早就憋足劲,要在新的形势下大干一场了,立即登车启程。
然而高氏废新法的心情比驿车的行进还要急切,司马光还在路上,她就派出使者拿着她的亲笔手书迎劳于途,再次询问今日设施以何为先。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奏明,她就迫不及待地遣散修筑京城的民夫,裁减皇城司的察事兵卒,停止宫廷工技制造,废导洛司,驱逐尤无善行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告诫中外官员不得苛暴聚敛,放宽民间保护马之规定。这些事全是她从宫中直接发号施令去办的,连宰相王珪等人事先都不知道。摧新复旧的闹剧,就这样由她一手拉开了序幕。
司马光和吕公著来到汴京,分别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和尚书左丞(都是副宰相)。在政治斗争中,思想舆论总是要成为实际行动的先导。因此,司马光下车伊始,高氏就把五月五日求谏诏令拿给他看,授意他先从舆论上打开缺口。司马光心领神会,立即把矛头首先指向求谏诏令,接连上了三道奏章要求修改,说诏中规定的六条限制,使得人们除非不言,一言必犯六条: 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怀有阴谋; 若本职之外稍有涉及,则谓之逾其本分; 陈国家安危大计,则谓之造谣生事、干扰机务; 若倡言与朝旨相合,则谓之迎合已行之令; 言新法不便当改,则谓之观望朝廷之意; 言民间愁苦可悯,则谓之眩惑流俗,沽名钓誉。如此则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六条必须去掉,新诏不但要贴于朝堂,还要颁诸天下。新的求谏诏令很快颁布,限制全部取消,反对派的言论立刻像火山喷发一样咆哮起来,不出一个月,上书言事者就数以千计,其中光是所谓农民所上的奏疏就达150道之多。舆论一经造足,废新法之事旋即提上了日程,到十二月间,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役法、保马法相继被废。与此同时,旧党中的主要干将刘挚、范纯仁、王岩叟、李常、孙觉、苏轼、苏辙等人被陆续招回朝中委以要职。
就像变法改革因遭到旧党的顽强反对进行得不一帆风顺一样,废除新法的活动在变法派成员们的抵制下,同样进行得不一帆风顺。长期与变法派斗争的实践,使高氏和司马光等人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政权上每放弃一块阵地,变法改革就会迈进一步; 政权上只要保留一个角落,就能或多或少地阻碍变法的进展。新法是与变法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变法派首领蔡確、章惇、韩缜仍身居相位,要想进一步废除新法,除了积聚、扩大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必须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变法派,从而把全部政权攫取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氏决定加强旧党在御史台、谏院中的力量。她在把王岩叟、刘挚、孙觉等人分别任命为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之后,又在元丰八年十月,不经过谏官须由知制诰以上官员荐举,然后由宰执大臣进奏的正规程序,直接下令任命唐淑向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右正言,苏辙为右司谏。宋代的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执掌纠察百官、肃正纲纪之权,它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而且有 “风闻奏事” 的特权,即不一定需要真凭实据,只要抓住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可以用来弹劾大臣,这一职能无疑大大强化了皇权,而使宰相的权力更受牵制。一班旧党的干将被接连安插进台谏之后,对变法派的参劾顿时掀起了更高的声浪。
最先暴露于他们炮火之下的是首相蔡確。赵顼死后,蔡確按惯例担任山陵使,主持丧葬事宜。据说当时规定在赵顼灵柩起程前的5天夜里,宰执大臣必须入宿宫中守灵,但蔡确没有来,刘挚就说是 “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 。朱光庭也揭发说: 灵柩出发时,蔡確不跟在后面,却先骑马跑出去数十里之远自图方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 。接着刘挚又说,蔡担任山陵使回朝,就应该引咎自劾,但他不顾廉耻,仍然赖着不退,以此为首共有十大罪状。朱光庭进一步扩大覆盖面,说蔡確、章惇、韩缜是三奸,不恭、不忠、不耻。到元祐元年(1086)二月,谏官们弹劾蔡確,要求将他罢黜的奏章已上了好几十道,言词越来越激烈,罪名也越加越多,蔡確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上表辞职。但他仍不甘心就此下台,表章中罗列了一些自己当宰相以来的功劳,哪知更惹起了谏官们的不满,在所有的罪名用尽之后,他们又搬出了新的理由。闰二月初一,王岩叟面见赵煦,说: “祖宗遗训宰相不可用南方人,今如蔡確、章惇都是南方人,恐怕有害于国。” 赵煦说: “他们都是旧臣。” 王岩叟说: “谁不是旧臣?” 赵煦说: “近日颇旱。” 王岩叟说: “皇上如此圣明,无致灾之理。只因朝廷中有蔡確这样的大奸小丑,所以天才旱。”在高氏眼里蔡確早就碍手碍脚了,见人们把他骂够了,第二天就将蔡確罢相,贬知陈州。
蔡確一下台,司马光当天就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这时司马光早已因病休假在家,他看到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还没废除,与西夏的和战问题还没解决,焦虑万分,叹着气说: “四害未除,我死不瞑目啊!” 同时写信给吕公著: “我自生病以来,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只有国事未有交代,现在只有托付给你了。”流露出无限的伤感,然而在接到当宰相的诰词之后,他的病却奇迹般地好了。高氏特别照顾他,免其入朝觐见,让他坐着轿子,三天一次到都堂议事,他却说: “不见君,不可以视事” ,每天坚持让儿子司马康扶着上朝论事。病居金陵的王安石听到消息怅然许久,深深叹道: “司马十二作相矣!”凭他对司马光思想性格的了解,他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将全部付诸东流了。
果然,司马光一当宰相,立即加快了废新法的步伐,同时也加紧了对新党的排挤。正月时,司马光连上两道奏章,要求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挖空心思说尽了免役法的坏处,却没想到这两道奏章竟自相矛盾。他既说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①,无有休息,对上户极为不利; 又转过头来说免役法虽使下户困苦,但对上户尤为方便。司马光说来自城乡居民的几千封奏章,无不言免役之害。可是经章惇检视,这些奏章中言免役之便者也有不少,司马光却隐瞒真相,不签贴整理。司马光这种前后不相照应,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漏洞和弄虚作假的伎俩,被任知枢密院事的变法派首领章惇一一捉住,敲点出来。司马光老羞成怒,与章惇把官司打到了高氏帘前。章惇自恃有理,对司马光冷讽热嘲,大加挖苦,甚至说将来我岂能陪着你挨刀吃剑。原来对章惇就反感的高氏这下子更火冒三丈,立即部署台谏向章讨伐。王岩叟说: “章惇轻佻浮薄,奸险凶悍,寡廉鲜耻,无大臣之礼,平常动不动说些诙谐下流的市井俚语,侮辱同事,今于帘前争役法,又出言不逊,凌上侮下,败群乱众,大概是见陛下用司马光作相,眼红忌妒,心怀怨恨,请求痛贬以谢天下。”闰二月二十三日,章惇被贬至汝州(今河南临汝)。一个月后,韩缜也被贬到颍昌府。
高氏和司马光等排挤新党是为了给废新法扫清障碍。到元祐三年底, 新法已废黜净尽, 新党分子也基本上全部驱逐出朝,有的被贬为地方官,有的被逐出政府,赶回老家闲住,有的被“编管”到偏远州县,失去迁居自由,高氏却仍不放松对他们的迫害打击。被“安置”到建州的原是王安石主要助手的吕惠卿后来曾说: “我被贬的9年间,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惟恐生病,让那些好事之徒抓住把柄,说我是因悲戚愁叹得病的。”如果说吕惠卿不敢喝凉水是由于他自身恐惧紧张导致的话,那么蔡確贬死于岭南则完全是高氏一手造成的。
蔡確被骂出朝廷后,第二年又被遞夺了官职、移贬安州(今湖北安陆)。此地有一处名胜,唤作车盖亭,蔡確有天前去游览,诗兴大发,连题10首,尽兴而归。却不料这10首诗被仇人知汉阳军吴处厚瞧见,种下了进一步挨整的祸根。原来,蔡確早年曾随吴处厚学过赋,作相之后,吴写信来请求照顾,蔡置之不理,王珪想提拔吴任馆阁之职,蔡又从中阻拦,吴处厚蓄意报复,就把蔡確的诗断章取义,滥加引申,上报朝廷,说: “诗中提到的郝甑山,就是唐高宗时封为甑山公的郝处俊,高宗想传位武则天,被郝谏阻,蔡確用此讥讪太皇太后。诗中说沧海扬尘,意思是希望时局大变。”谏官吴安诗、范祖禹、王岩叟立即上书弹劾,皆言蔡確怀怨谤讪,罪大该杀。宰相范纯仁却认为仅凭暧昧不清的语言文字诛杀大臣简直太过分了。文彦博提议将蔡確贬到岭南,范纯仁向另一位宰相吕大防说: “此路自丁晋公(谓)之后,荆棘六七十年了,一旦重开,我辈恐怕也免不了。” 然而高氏却坚持非痛贬蔡確不可,她采纳文彦博的建议,发布命令,贬蔡確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刘挚说蔡確有老母在家,不要像唐朝柳宗元、刘禹锡贬至播州那样,将他整得太惨,吕大防也请求贬得近一些。哪知高氏勃然怒道: “蔡確肯定死不了!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当晚就差出入内供奉官裴彦臣,把蔡確押到了新州。新州是岭南蛮荒之地,瘴气氤氲,潮湿闷热,人极易生病,所以贬至此地是北宋最重的处罚。蔡確至此,很快患病,不几年就死在那里。一些不同意贬蔡確的官员也跟着倒了霉,御史中丞李常说了句 “以诗罪確,非敦厚风俗之举” ,被贬知邓州; 中书舍人彭汝砺说“这是罗织罪名的开始” ,被贬知徐州; 侍御史盛陶说 “不可长告讦之风” ,也贬知汝州。高氏之所以借题发挥,痛贬蔡確,除了恼怒蔡確谤讪,还另外有一层深意。她后来解释说:“皇上乃先帝长子,子继父业,理所应当,他蔡確有何功劳,竟三番五次地说自己有策立之勋?假若他以后东山再起,欺罔上下,岂不为社稷祸害!我怕皇上年少制驭不了他,所以才借机将他远窜,这全是为社稷着想哩。”原来她早已存心要把蔡確置于死地了。苏轼过去也因写诗被治过罪,挨整挨出了经验,当时曾向高氏秘进一言: “朝廷若放宽对蔡確的处置,则对皇帝的孝治有所不足; 若加重处罚,则对太皇太后的仁政稍有损伤。莫若由皇帝降敕痛贬而太皇太后特加宽贷,仁孝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对高氏来说,这样做既可以达到目的,又能收到宽厚仁恕的美名,确是一条妙计。可是她整人心切,竟连策略都顾不得讲究了。
蔡確事件后,高氏为了使变法派永无翻身之日,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打击。她授意梁焘,开具了一份新党分子的黑名单,把安焘、邢恕等47人列为蔡确的亲党,把章惇、吕惠卿、沈括等30人列为王安石的亲党,然后她拿着这份名单对宰执大臣说: “蔡確奸党仍有不少窃居朝官。” 范纯仁说: “朋党难辨,可别误伤好人。”高氏很不高兴,梁焘竟弹劾范纯仁也是蔡確之党,高氏遂将范纯仁罢相,贬知颍昌府。“亲党” 的黑名单也在朝堂张贴出来,告诫人们永远不准这些人再做官。
范纯仁的下场以及蔡確事件中彭汝砺、盛陶等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更加证明了高氏对变法派的憎恶,任何人不能替变法派说半句好话,任何人不能阻碍她对变法派的打击,哪怕这些人都曾经是旧党中的重要成员,都曾为她废新法逐新党效过劳、出过力。这些事同时也证明,所谓的旧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牵涉到利害冲突的时候,矛盾斗争同样会在他们中间展开。
事实上,这种矛盾斗争早在旧党成员上台伊始就已展开了。这是因为,尽管对新法的一致反对和受变法派排挤的共同遭遇曾一度使旧党们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但他们内部在如何对待新法和如何处置新党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例如对于免役法,范纯仁、王岩叟、李常等人就不主张全部废除,苏轼还与司马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有一天,经过多次争论之后,在政事堂上苏轼再次提出了支持免役法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有些怒形于色,苏轼毫不客气地说: “当年韩魏公(琦)刺配陕西义勇兵,你当谏官,极力反对,韩公不乐,你也不顾。我过去曾几次听你讲起此事。难道说今天你当了宰相,反而也不许我尽言吗?” 司马光尴尬地笑了笑,向苏轼表示歉意,但最后仍废除了免役法,气得苏轼大骂: “司马牛!司马牛!” 至于对新党分子的打击,旧党中的许多人或者出于公正之心,或者考虑到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总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反对过分打击新党,像范纯仁对吕大防所说的“我辈恐怕也免不了”的话,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这些政治观点的分歧,再加上旧党分子中早就存在的个人恩怨和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利害冲突,终于使他们演出了一场激烈的党争闹剧。
冲突最先在苏轼和担任赵煦师傅的程颐之间展开。苏轼很瞧不起程颐一举一动都照搬书本的迂腐气十足的为人,常当众奚落他。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死的时候,百官正举行明堂大礼,大伙都想在庆礼结束后去给司马光吊唁,程颐以为不可,并引经据典地说: “孔子在同一天里哭则不歌。”有人驳难:“孔子说哭则不歌,并没说歌则不哭。”苏轼接过话头冷笑着讽刺道: “这大概是枉死西市的叔孙通新制的礼仪吧。”众人大笑,程颐下不来台,两人的嫌隙更加深了。程颐的学生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就借机弹劾苏轼,为老师报仇。从此朝内大臣以气相争、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 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他弟弟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 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结为一伙,号称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此党反对的,彼党必支持,彼党支持的,此党必反对,意气用事,不顾是非,乱哄哄闹成一团。
虽然高氏曾经讲过 “要一心为国,不要拉帮结党” 的话,但总起来看,她对党争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她不像赵煦那样反感党争,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对党争忧心忡忡,她不在乎党争如何激烈,如何荒唐,甚至有时还会给党争煽风点火,扩大党争的规模。如朱光庭抓住苏轼给馆职考试出的试题的一些话,弹劾苏轼,吏部尚书兼侍读傅尧俞和王岩叟也说试题不当,她说: “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只是党附朱光庭罢了。”吓得傅、王赶紧要求辞职。然后她再下诏对试题批评一番,请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依然上班供职。这显然是在利用党争各方的矛盾来维护自己仲裁一切的权威。因此,她对党争各方孰是孰非的评判,始终坚持了一条标准,即任何一方只要不妨碍她垂帘听政,不蔑视她的权威,无论争得多么激烈、多么荒唐,她都能容忍。但如果某一党对她稍有妨碍,或者稍有指责,无论他是什么人,她都会立即翻脸,给个颜色看。
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推荐他当了崇政殿说书,即赵煦的老师。元祐二年(1069)八月的时候,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殿听课。这事宰执大臣们连过问都没有一声,高氏也照旧上殿视事。程颐看不下去,就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 “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吕公著回答: “不知道。”程颐说: “二圣(即赵煦和高氏)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行吗?” 第二天吕公著等才去向赵煦问疾。程颐则因这番多嘴得罪了高氏,不几天就被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一个月后,贾易也被加上“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 的罪名,被贬出朝。到了元祐七年(1092),宰相又建议任命程颐担任官职,高氏仍怀恨在心,不肯答应。
刘挚与吕大防同任宰相,两人很早就有矛盾。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见许多大事是吕大防说了算,便极力巴结吕,弹劾刘挚,说他惯于笼络士人,不问善恶,即便是赃污久废之人,也甜言蜜语拉到身边。并列出刘挚一党的名单,共30人。右正言虞策也揭露刘挚包庇犯了法的亲戚王巩。因王巩做官是苏辙推荐的,所以刘挚和苏辙同时上章辞职,高氏却单单降诏,挽留苏辙而把刘挚罢相,贬知郓州。刘挚在旧党中几乎是仅次于司马光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废除新法还是弹劾蔡确、章惇,他都当急先锋,高氏也曾对他极其赏识。难道这次罢相真的因为他结党包庇吗?不是的,赵煦后来与吕大防的一次谈话透露了底细,“弹劾刘挚的奏章已有18道,但罢他不是因为王巩之事,而是由于与邢恕通信和接纳章惇之子的缘故。”原来蔡确被贬后,邢恕也被贬为监永州酒税。邢恕向来与刘挚关系不错,坐船经过汴京时,写信向刘挚告别。刘挚复信,安慰说: “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到那里去为国自爱,等待休复吧。”送信的人来到汴河边,向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打听: “邢恕的船在哪儿?”不料茹东济是个奸诈小人,曾几次有求于刘挚却被拒绝,心怀怨恨,就把信骗到手,抄录了一份送给了郑雍和杨畏。这两人正找岔子倾陷刘挚哩,见信如获至宝,立即加上注释献给了高氏。注释说: “休复二字出自 《周易》 ,复就是 ‘复子明辟’ 之复,意思是刘挚劝邢恕等待将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还政给赵煦)。” 同时揭露章惇的几个儿子一直与刘挚保持联系。高氏大怒,宣来刘挚厉声训道: “有人说你结交奸人,为将来打算。你应该一心效忠王室,像章惇这种人,即使让他当宰相,他也未必满足。”刘挚惊恐万状,慌忙上书自辩,可是一切都晚了。当初罢免刘挚的诏令起草好之后,被给事中朱光庭退了回来,并说: “刘挚是有功大臣,一旦因猜疑而罢,天下却不见他有什么错。”有人便说他结党刘挚,也被贬知亳州。王岩叟求见高氏,说: “臣之所以欲有所言,不是为了一个刘挚,而是为陛下爱惜腹心之人。言事之官未必都忠直,杨畏乃是吕惠卿的党徒,他只是想除掉陛下的心腹,为奸邪开路罢了。”高氏说: “垂帘之初,刘挚排斥奸邪,确为忠实,但这两件事他很不该做。”从此直到死去,刘挚再也没有迈进过朝廷。
高氏虽在垂帘之初表白说: “我生性好静,只因皇上年幼,权同听政,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也非国家盛事。” 然而七八年过去,赵煦都已经结了婚,不能算小了,人们仍没有看见高氏有一丝一毫还政退位的意思,看见的只是对她稍有指责、或可能希望她复辟还政的大臣被接连逐出朝廷。她的权力欲竟是如此强烈,大臣们需要做的只是匍匐在她的脚下俯首听命而已,凡有奏事,都只向她禀报,名为皇帝的赵煦却被冷落在了一边。赵煦后来愤愤不平地对人讲: “元祐垂帘时,我每天看到的只是大臣的脊背和屁股,他们的脑袋全转到太皇太后那里去了。”有时赵煦偶尔问件事,大臣们竟连答理的都没有,甚至他生病好几天了,高氏都不兴说一声,大臣们也无人过问。这使赵煦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中充满了对高氏及其大臣的怨恨,但在高氏的威慑下,他表示不满的武器只能是沉默而已。高氏有一次问他: “大臣们奏事的时候,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怎么连句话都没有?”赵煦答道: “娘娘已处理过了,叫臣又说什么呢?”
一个如此热衷于权力的人,在垂帘听政、独揽一切大权的九年间,居然仍能似以往一样,对待个人名利和高家的地位待遇保持了谦虚的美德,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事实。
高氏的伯父高遵裕,自英宗时起一直在宋西北边疆与西夏作战,曾因几次赢得胜利,升任庆州知州。元丰四年(1081)神宗赵顼派宦官李宪为统帅向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王中正出河东路,计划由环庆、泾原两路会师先取灵州,其他几路以夏州为会合点,再取怀州,最后五路会攻兴州,要一举讨平西夏。刘昌祚率兵五万,受高遵裕节制,首先向夏境挺进,在堪哥平磨哆隘口(在灵州南百余里)击败夏军,乘胜抵达灵州城下,发动猛攻,几乎攻克。高遵裕却嫉妒刘昌祚独得大功,命他停止攻城,等待后兵。可是等高遵裕来到,夏兵已作好防御准备,以致围城18天仍未攻下。夏人决开黄河淹灌宋军营垒,又截断宋军粮饷运输线,宋军因冻溺饥饿而死者甚多,被迫溃退。高遵裕率领的8.7万人,只剩下了1.3万。其他各路也损兵折将,狼狈撤回。高遵裕因此被贬为郢州团练副使。高氏垂帘听政后,蔡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讨好高氏,有天提议恢复高遵裕的官职,高氏板着面孔说:“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生灵,先帝半夜得到战报,焦虑得起床来回踱步,达旦不寐,精神受了很大刺激,终于病故,这祸就是遵裕惹下的,他能免于一死,就已是万幸了。先帝尸骨未寒,我岂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蔡确悚然而止。
对待高家的其他亲戚,包括自己的母亲,高氏同样不肯顾私恩。有一年元霄节举行灯宴,按规定高氏的母亲曹氏可以入宫观览,但高氏说: “夫人若登楼观灯,皇上必定对她加礼致敬,这样就会因我的缘故越犯典制,我于心十分不安。” 只是命人给母亲送去几盏宫灯,请她在自己家里观赏,后来年年如此。 高氏的侄子高公绘、 高公纪按规定可以升为观察使。高氏也极力阻拦。赵煦请求了几次,高氏只同意提升一级,以后在整个垂帘期间,再没升过。
高氏本人也能做到谦虚俭朴。有年殿试举人,有关部门请求依照章献明肃刘皇后天圣年间的做法,请赵煦和高氏一同御殿,高氏不同意。后来大臣又请求她在文德殿举行册封太皇太后的典礼,高氏也说: “文德殿是天子的正堂,岂是女主应当临御的?我只在崇政殿就可以了。” 文思院每年进贡给皇帝御用的物品,无论大小,她终身不取一件。
对于宫中的宦官、宫女,高氏控制得更是严格,不准他们干预政治。垂帘之初,被她认为尤无善行驱逐出宫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后来又托了赵顼乳母的关系向高氏求情,企图再得任用。高氏见那乳母进来,劈头就问: “你来干什么?难道是为宋用臣等人游说的吗?并且你也想像以前那样,求皇上内降诏旨干扰国政吗?你听好了: 若再敢这样,我就要你的脑袋!”乳母吓得要死,半个字没敢说,就乖乖溜出宫去。
由于高氏具有了这种美德,更由于她全盘推翻新法,起用元老旧臣,最大限度地迎合并满足了那些在变法期间受到抑制的官僚贵族、豪强兼并者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高度推崇,被称誉为“女中尧舜” 。
然而,既然变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愿望,反改革反变法只是代表了一小撮在政治上、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贵族、豪强兼并者的腐朽、落后的利益,那么,在高氏把持下进行的 “元祐更化” ,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气势汹汹,都只能是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也就必然遭到社会的唾弃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早在“元祐更化”刚刚开始的时候,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了 “更化”必定失败,案子必定会被重新翻过来。有人对司马光说: “你拿 ‘以母改子’ 当旗号废新法,别人就不会拿 ‘以子继父’ 为旗号恢复新法吗?” 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 “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鸿胪卿常安民写信给吕公著: “如果用十个人制一只虎,人必胜,若以一人制十虎,则虎必胜,现在是数十个人制几千只虎,只怕祸不旋踵了。” 吕公著没有司马光那样的主观武断,喊不出惊人的豪言壮语,只能默然以对。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如常安民所言,变法派这只老虎虽然暂时被关进了笼子,驱逐进深山,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仍是那样的强大,相比之下,旧党们的力量又是那样的渺小,一旦政治风云再次突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发生变动,这只老虎一定会挣脱牢笼,奔出深山,再度猛扑回来的。
形势的发展,不仅使常安民、吕公著有所警觉,就连顽固透顶的高氏也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这使他们不寒而慄,心惊胆颤。为了防止这一危险早日降临,她咬定权力不放松,绞尽脑汁向少年天子赵煦灌输她自己终生信奉的政治信条。说祖宗之法是多么多么的美妙,只要能尽行祖宗家法,就足能致天下太平,使百姓咸被其泽; 还说赵顼晚年是如何如何地懊悔变法,有时痛苦得悔泪横流,并说如果赵顼仍然在世也必能尽废新法。但无论她怎样讲,赵煦始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无声的抵抗在高氏及其大臣们看来,甚至比晴空霹雳还要惊心动魄。于是,当高氏躯壳中最后一缕生命之火快要熄灭的时候,她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前景,简直比死神的来临还要恐惧。
元祐八年(1093)七月初一,范纯仁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范的复起丝毫不是高氏对他的政治观点放弃了恶感的缘故,而是认为范纯仁能像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在即将到来的风云变幻中采取符合自己意愿的行动。她召见范纯仁时说: “令尊仲淹,在章献明肃太后垂帘时,劝章献对仁宗尽母亲之道,等到仁宗亲政,又劝仁宗尽儿子之道,真可谓忠臣,我相信你必能继承先人。” 范纯仁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 “敢不尽忠!”
八月,高氏患病,很快加重。她把范纯仁、吕大防召到榻前无限凄怆地交代后事: “我觉着病情更重,只怕快要与你们长辞了,你们要好好辅佐官家。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国政,你们回想一下,9年来,我曾做过一件施恩高家的事吗?我怀着一颗赤诚至公之心,为国操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得快要死了,我都顾不上看一看啊!” 说着已泣不成声。众人陪着抹了一会儿眼泪,高氏又说: “先帝晚年追悔往事,甚至泣下,这事官家应该深知,老身死后,肯定有很多挑拨官家的,一个不要去听。你们也要早早退避,让官家另外用一番人。” 说罢命左右侍者端出社饭①,赐给众人,并说:“明年社饭时,希望你们仍然记着老身。”
九月,高氏病故,享年62岁。次年二月,葬于永厚陵。
注释
① 北宋政府把全国人户分为主户和客户(即佃户)两类。又依资产高下把主户分为五等,一、二等称上户,三等称中户,四、五等称下户。
① 社饭,八月祭祀土神时供的饭食,宋代的做法是用猪、羊肉、内脏等切成棋子块状,加滋味调和,铺于饭上。
相关参考
宋英宗怎么死的宋朝英宗赵曙的皇后是谁儿子宋神宗赵顼(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针,宋英宗赵曙长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吴荣王赵颢字仲明,初名仲糺,宋英宗赵曙次子
宋英宗是宋朝的第五位皇帝,是宋仁宗的继承人。宋英宗仅在位五年,活了三十六岁,后来便英年去世了。历史上有记载的女人,有皇后高滔滔、修容张氏、昭仪鲍氏和贵仪张氏。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少。在这四位女子之中,宋...
宋英宗的身体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好,他一开始继位的时候身体就有问题,大致上应该就是有什么隐疾了。在史书上对宋英宗的死记载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史书里说宋英宗是“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
宋英宗的身体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好,他一开始继位的时候身体就有问题,大致上应该就是有什么隐疾了。在史书上对宋英宗的死记载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史书里说宋英宗是“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
宋英宗赵曙最爱的女人是谁宋英宗在位时间很短,仅有四年,因此他的后妃也不多,有记载的仅有皇后高滔滔、修容张氏、昭仪鲍氏和贵仪张氏等四人,那么宋英宗赵曙最爱的女人是谁呢?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的画像宋英宗最爱
宋徽宗父亲宋徽宗父亲叫赵顼,他是宋英宗的长子,是宋英宗赵曙和皇后高氏的长子。赵顼从小就喜欢读书,在他还是太子时就非常的爱读《韩非子》这样的书籍,对于法家的观点非常的赞同,他也觉得富国必先强兵,他甚至读
神宗赵顼皇后向氏治平三年(1066)春,宋英宗赵曙的长子颍王赵顼已近18周岁,按礼俗早已到了纳妃大婚的年龄,宫中派出了一些使者到大臣之家访求可以匹配的姑娘。赵顼的老师记室韩维对此事更是关心,为了明确选
宋朝人物中文名:赵曙别名:赵宗实,宋英宗国籍:北宋民族:汉族出生地:开封出生日期:1032年2月16日逝世日期:1067年1月25日职业:皇帝主要成就:命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位时间:1063年—1
有人篡权也要当皇帝,也有人被推上龙椅却不愿意坐,真是什么样的奇葩都有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不愿意当皇帝的都有谁吧!宋英宗赵曙英宗赵曙是宋朝第五帝,是宋仁宗弟弟濮王的儿子。仁宗久未得子,后得二子又相继
有人篡权也要当皇帝,也有人被推上龙椅却不愿意坐,真是什么样的奇葩都有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不愿意当皇帝的都有谁吧!宋英宗赵曙英宗赵曙是宋朝第五帝,是宋仁宗弟弟濮王的儿子。仁宗久未得子,后得二子又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