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Posted 工人
篇首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法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在法国里昂先后发生了两次工人起义。这两次起义是工人阶级为反对他们的直接剥削者资产阶级,并维护自身利益而举行的最早的起义。它表明,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而,无论在法国工人运动史或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法国工人阶级积极地参加了历次革命运动。但是,在这些斗争中,工人只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里昂工人起义表明,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第一次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因此,里昂工人起义在法国历史上也是重要事件,从此以后,资产阶级便不得不认真对付工人阶级了。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政府极力保护大地主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和特权,使经济发展受到不良的影响。1830年7月革命后,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制。工人阶级虽然在七月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现实生活使他们产生了初步的阶级意识。
进入十九世纪后,法国的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手工业生产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但仍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三十年代初,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工业企业是10人以下的手工作坊,大量使用机器的工厂为数甚少。在这种条件下,工人的斗争仍处在自发阶段,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捣毁机器和排挤外籍工人。他们还不了解自身所受痛苦的根源,不懂得应当直接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以丝织工人为主体、有各行各业工人参加的里昂工人起义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
丝织业从十五世纪在里昂兴盛起来,到十七、十八世纪,已成为里昂经济生活的支柱。丝织业使里昂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并为法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当时法国的全部出口商品中,里昂的丝织品约占1/3。因而,里昂有法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里昂的面貌有所改变。但直到1831年,里昂的丝织业仍旧停留在恩格斯所说的工业生产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即“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①。当时里昂约有8千个丝织业作坊,每个作坊通常有2至6台织机。作坊主便是师傅,织机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全家老少参加劳动,人力不足时则雇用帮工、学徒和其他辅助工。他们除织机外,不拥有其它生产手段和资金。生产的原料由包买商提供,制成产品后,仍由包买商负责销售。作坊师傅按产品数量向包买商取得工价,与作坊内的全体人员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包买商不从事劳动,利用资本对作坊师傅和其他工人进行剥削。帮工一无所有,是仅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无产者。而作坊师傅则是手工业劳动者,与帮工一样受到包买商的盘剥。这两部分人的经济地位虽不尽相同,但在反对包买商的斗争中,他们的利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早在1825年,里昂已出现了最早的工人组织“互助社”。这个组织的成员仅限于作坊师傅,其宗旨是在反对包买商的斗争中相互支援,互通消息,在生产中互相帮助。为了不触犯刑法关于结社的规定,互助社通常分为20人以下的小组活动。尽管这个组织仍带有某些行会色彩,却是组织工人进行共同斗争的团体,所以它的影响不断扩大。
里昂的丝织业在波及范围极广的1825—1826年经济危机中遭受沉重的打击,一半以上的织机被迫停产,失业工人一度占工人总数的60%以上。1827年后略有回升,直到1830年,尚无显著发展。七月王朝为增加国库收入,满足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发财致富的愿望,采取了提高间接税的手段,致使物价上涨,食盐、酒等食品都增了税,房租也随之上涨,工人的负担因而愈加沉重。包买商为了压跨竞争的对手,往往以降低工价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广大丝织工人深受其害,他们的收入明显低于七月革命前的水平,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工人每天约工作15到16小时,菲薄的工资不足维持生计。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屋中,衣衫褴褛,饮食粗劣,疾病流行。工人的愤懑情绪与日俱增。
包买商支付的工价是工人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工价的高低是工人生死攸关的问题。1831年初,一场以提高工价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在里昂逐渐酝酿成熟。1月19日,失业工人举行游行。2月,工人征集签名,向众议院递送请愿书,要求改组劳资调解委员会,解决提高工价问题,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多达3千余人。5月前后,气氛渐趋紧张,各类集会日益增多。4月28日,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宣讲团到达里昂,连续作了5次公开讲演。工人踊跃前往听讲,最多时达3千余人。圣西门主义者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对工人深表同情,并向他们描绘一幅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对工人颇有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燃旺了工人们的斗争激情。6月,共和派在里昂发行两种报刊,对七月王朝政府进行抨击。与此同时,《人民之友社》①也在里昂积极活动。这些政治派别的活动,使里昂工人以经济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增添了政治色彩。
10月8日,在丝织工人聚居的棕十字区,举行了有300余名作坊师傅参加的集会,决定推选80名代表,组成向包买商进行斗争的领导机构。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当局出面组织一个由工人代表和包买商代表共同参加的协商机构,就最低工价进行磋商。当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表示愿意就此进行斡旋,但协商会议迟迟不举行。10月17日,失去耐心的150余名工人高唱“马赛曲”上街游行。省长迪摩拉本人是一个矿业主,他作为官吏兼资本家,当然不会支持工人,但他慑于工人的强大压力,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不敢采取强硬措施。于是,他玩弄两面手法,力图赢得工人的好感。10月21日,工人和包买商的代表在省长主持下举行首次协商,未达成协议。工人们再次上街游行,对包买商施加压力。工人的行动吓坏了当局。省长一面下令加强防范,一面尽力撮合双方达成协议。
10月25日是双方代表就最低工价标准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的日子。这天清晨, 6千余名丝织工人排成整齐的百人方队,秩序井然地向会场进发,给自己的代表以无声的支持。双方代表经过4小时讨论,终于订出了最低工价标准。消息传出,停留在会场外面的工人们欣喜若狂,高呼“工人万岁!”与此同时,他们还高呼“省长万岁!”他们以为省长同情工人的疾苦,是他的居间调停才促成了协议的达成。不难看出,里昂工人的阶级意识尚处在觉醒的初期,他们只看到包买商对他们的直接剥削,看不到七月王朝政府的阶级实质;他们不但不反对迪摩拉省长这种伪善的官吏,反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企图借助他的力量去同包买商进行斗争。里昂工人政治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是里昂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最低工价标准的协议达成后,包买商拒不执行,并派人去巴黎诬告工人。工人多次集会商量对策,决定拒绝以低于标准的工价进行生产。11月17日,七月王朝的商业大臣在巴黎宣布里昂工人与包买商拟定的最低工价标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包买商更加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彻底撕毁协议。面对包买商的猖狂挑畔,工人们怒不可遏,决定从当天起罢工一周,并定于11月21日举行大型集会,以示抗议。
当局闻讯后,立即作了镇压的部署。11月21日上午,数千工人在棕十字区集合,走向包买商聚居的卡皮森区,途中与国民自卫军相遇。国民自卫军在事先不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向工人队伍开枪,当场打死3人,打伤10余人。工人们被迫折回棕十字区自卫,一部分人修筑街垒,挖掘战壕,一部分人抬着同伴的尸体在街上游行,号召工人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棕十字区的丝织工人纷纷拿起棍棒、长矛、大刀、铁锹、鹤嘴锄奔上街垒。布罗托等其它区的制帽等行业的工人也赶来支援。下午,工人与军队交火。工人的街垒上飘扬着黑旗,其中一面写着:“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这个口号反映出终日不得温饱是工人们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要求。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省长带着一名将军前来劝说工人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正当省长要向工人发表讲话时,政府军再次发动进攻。工人们对省长的意图发生怀疑,遂将他和将军暂时扣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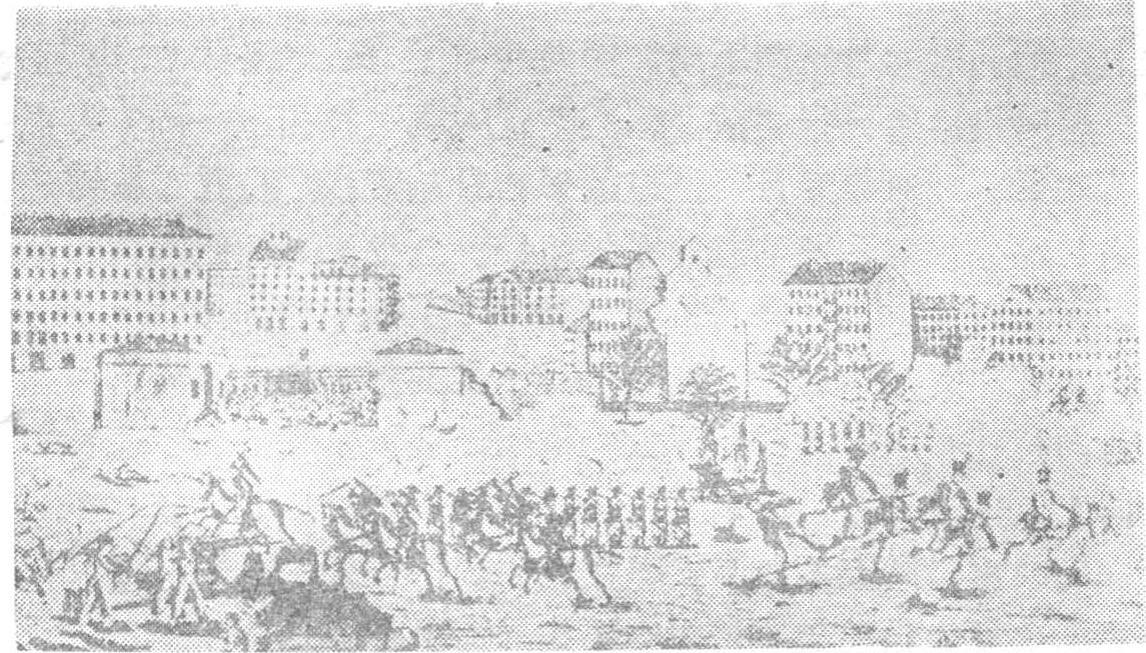
里昂棕十字区。1831年11月21日、22日起义工人和政府军冲突的情景。
罢工一经变成武装起义,互助社便失去了作用,领导工人进行战斗的主要是罗讷义勇军的成员。1831年1月,在拉法耶特的影响和支持下,里昂曾组织过一支志愿部队,称为罗讷义勇军,向维也纳会议后划归撒丁王国的萨瓦进军,争取萨瓦回归法国。里昂600余名失业和穷苦的丝织工人参加了这支部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拿破仑时期当过兵、打过仗, 军事素质较高。在政治上,他们对七月王朝不满,倾向共和主义。部队在边境受阻,返回里昂后自行解散。但其负责人之一拉孔布与许多人仍保持着联系。1831年8月,里昂的形势日趋紧张,拉孔布秘密进行联络,部分恢复了罗讷志愿军的组织。这批工人的组织性和战斗性较强,而且有实战经验,在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装冲突开始后,拉孔布便成了主要指挥者。当晚,被扣的省长向拉孔布表示,如获释放,他保证让军事指挥官罗盖将军停止向工人进攻,并迫使包买商执行关于工价的协议。拉孔布身上同样反映出里昂工人的不成熟性。他轻信省长的保证,下令将其释放。次日凌晨,与省长同时被扣的那位将军也获释。
11月22日,战斗继续进行,起义工人击退了政府军的进攻,转入反攻。各行各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加入起义行列。里昂工人在战斗中实现了自身的团结。当天黄昏,除市政厅、省长公署等少数据点外,起义工人控制了全城。政府的文武官员于当日深夜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退。罗盖将军率残部撤离里昂,文官集中到省长公署。11月23日凌晨,市政厅被起义工人占领。
起义工人既无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不认识反动政府的本质,因而当起义工人控制了全城,反动政府事实上已被摧垮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处置用鲜血争来的胜利。反而是省长迪摩拉把拉孔布召到省长公署,授权他去市政厅主持市政事务。拉孔布和许多工人一样,认为事端是军方挑起的,省长是同情工人的。他到达市政厅后,组织了一个以罗讷志愿军成员为主的领导班子。由于这个班子设在原国民自卫军司令部办公室内,所以称为“临时司令部”。拉孔布想到的不是扩大战果,肃清残敌,而是派人到各区加强巡逻,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以表明起义工人并非匪徒。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去监狱释放因负债而入狱的贫民。
临时司令部建立不久,有人送来了一份事先拟就的告市民书,建议由拉孔布等签署后发布。告市民书写道:“狡诈的官吏们事实上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会议,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自卫队。今后,内阁大臣们再也不能强迫我们听从他们的鬼把戏了。”这份告市民书实质上是推翻反动政府的宣言书,经拉孔布等在场的临时司令部成员讨论同意后,送印刷厂付印。数小时后,告市民书已经印好,少量已经张贴。这时有人指出,草拟这份文件的是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保皇派分子。拉孔布等人认为与保皇派发生干系有损于他们的名声,况且推翻政府并不是他们的本意,遂下令立即停止张贴,并立即拟就一个通告,断然否认告市民书。
告市民书在棕十字区贴出后,起义工人的反应冷淡,因为其中并未提到工人的主要斗争目标——最低工价标准。随后的那份通告贴出后,起义工人更感茫然。由此可见,这次起义虽具有政治色彩,但这些政治色彩大多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就工人自身而言,他们争取的主要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并不鲜明。
11月24日,省长迪摩拉来到市政厅,改组了临时司令部,安插了一些政府官员。工人竟未表示反对。省长继续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将重新召开会议,讨论最低工价标准,在包买商接受最低工价标准之前,包买商实付的工价与应付工价的差额,由政府支付。他还许诺拨款救济赤贫工人。他以这些为条件,要求工人复工。起义工人认为斗争目的即将达到,遂于11月26日开始复工。
七月王朝政府对里昂工人起义甚感恐慌,立即派兵镇压。11月29日,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和苏尔特元帅率兵到达里昂郊外。12月3日进入市区。部分起义工人继续整修街垒,准备抵抗,但因无人领导而未能再次进行战斗。临时司令部无声无息地自行解散。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起义在阶级敌人的欺骗和镇压下失败了。
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
1831年11月的起义失败了。里昂工人热切盼望的最低工价标准成为泡影,生活丝毫没有改善。但是,工人的血没有白流,战斗锻炼和教育了他们。他们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自1832年起,互助社组织逐步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工人,领导体系也较过去完善。每小组(20人以下)选出两名代表,若干组的代表组成中心组,各中心组的组长联席会议是全社的最高领导机关。1834年初,中心组长联席会议改称执行委员会。在互助社的领导下,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经常向包买商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和派的活动也日趋活跃。各种团体日益增多,如“人权社”、“进步社”、“独立者社”、“自由人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权社”,“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人权社”的成员。“进步社”的领导人拉格朗热十分同情工人,在工人中享有一定的威望。
七月王朝对工人和共和派的结社活动十分恼火,于1834年2月向议会提出新的法案,在刑法禁止20人以上结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20人以下的结社活动也在被禁之列。这项法案虽然尚未通过,但各地均已获悉,人民普遍表示愤慨。里昂的互助社本来是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标的工人团体,而共和派的各个团体则致力于政治斗争,所以往常彼此虽有影响,却并无紧密的联系。现在,反对禁止结社法的斗争把它们团结起来了。
1834年初,里昂的包买商将每一欧那①长毛绒的工价降低了25生丁。这个数字并不大,受到直接影响的工人也只有1,200余人。但工人的觉悟已经提高,他们开始认识到工人的命运是彼此相连的,对包买商的斗争是全体工人的事。在互助社的号召下,里昂的全体丝织工人从2月12日起实行罢工。17日,数百名工人在泰罗广场集合,准备向市政厅进发。当局派军队鸣枪示警,集会被冲散。包买商在当局支持下拒不让步。部分工人因罢工期间生活来源断绝而十分困难。互助社的执行委员会遂下令于2月22日复工,结束了这次为期10天的罢工。这次罢工虽未取得积极成果,但对包买商和当局无疑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狡黠的反动当局在罢工高潮中借口不插手劳资纠纷,表面上袖手旁观,实际上支持包买商的强硬态度。罢工结束后,反动当局凶相毕露,悍然逮捕了6名工人。工人们被当局的卑劣行径所激怒,一场新的斗争已在酝酿之中。正在此时,3月25日传来消息,扩大禁止结社范围的新法案已在议会通过。根据这项法案,工人不仅不能组织新的团体,原有的团体也将被迫解散。导火线就这样被点燃了。互助社与人权社等共和派团体共同组成一个总委员会,具体领导工人的斗争。当局定于4月5日开始审讯6名被捕工人,总委员会决定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不难看出,1831年,起义工人争取的主要是经济目标,而1834年,工人争取的不再只是经济目标,主要的已是政治目标。这说明,工人运动在向前发展。
4月5日,工人在法庭所在地圣约翰广场示威时,一名工人被枪杀。次日,8千余名工人举行抬尸游行,在全市引起巨大反响。法庭不得不宣布将审讯推迟到4月9日。4月8日夜间,总委员会举行会议,对情况作了分析,估计反动当局次日可能使用武力,遂决定以“结社、抵抗和勇敢”为口号,坚决给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以反击,但不主动挑起武装冲突。会议任命拉格朗热等人为总指挥。
形势日趋紧张,一场恶斗即将爆发。法院院长担心酿成流血事件,向当局提议移地审讯,以免触发冲突。当局未予采纳。1831年11月的工人起义把政府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局事后在里昂全力加强戒备,修筑了许多碉堡和据点,配置了许多火炮,警卫部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当局凭借这些镇压手段,企图伺机进行暴力镇压,扑灭里昂的工人运动。所以,4月8日夜间当局在部署兵力时,并未采取任何避免发生冲突的预防性措施。恰恰相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在内的1万余人控制了全市所有战略要点。当局还派便衣警察混在工人当中进行煽动。很显然,反动当局蓄意要血洗里昂。
4月9日,大批工人拥向法庭,有的进入院内,有的留在广场上。审讯正在进行时,军队突然向工人开枪。工人立即奔向工人居住点和市中心,修筑街垒,进行抵抗。大多数工人没有武器,而且事先虽预计到发生冲突,却缺乏周详的准备,所以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最初的混乱过去后,全市形成了6个起义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市中心的哥德利埃教堂。拉格朗热在这里指挥。他冒着炮火,往返于各个街垒之间,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和赞赏。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前来支援,有的在街垒中与反动军队作战,有的赶制弹药,用织机上的零件熔制子弹,有的抢救照看伤员。工人们举起写着“不共和毋宁死”的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反动的七月王朝政府。当局命令军队“街上见人格杀勿论”。军队以火炮轰击起义工人的街垒,放火焚烧工人的住房,并闯入民宅虐杀无辜平民,连病人和妇孺老弱也不放过。战斗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条件下进行的,到10日夜间,当局已明显占了上风,但起义工人们仍顽强抵抗。据路易·勃朗后来分析,这时如要结束战斗,对当局来说并不困难,但当局蓄意拖延,为的是在战火中杀害更多的起义工人。4月13日,最后一批街垒被军队攻陷,最后一批起义工人在哥德利埃教堂前英勇献身,为工人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在火海血泊中失败了。
里昂工人起义的意义及其失败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里昂工人起义作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称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黑旗上所写的“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口号”①。恩格斯说:“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②列宁在谈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时说道:“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一次或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积累)正在成长、发展、学习、得到训练并且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正在从自发性走向计划性,从领导各阶级的一种情绪走向领导各阶级的客观地位,从自发发动走向持久的斗争。”①
里昂工人起义发生在法国工业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这时的工人运动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并把两者结合起来。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鲜明地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将这两次起义作一个对比,不难看出,1834年的里昂工人阶级比1831年时成熟一些。他们初步认识到政府的阶级本质,组织程度有了提高,斗争目标的政治色彩较浓。
尽管如此,当时的工人运动毕竟仍然处在早期阶段。除了七月王朝政府的狡诈欺骗和残酷镇压外,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不难从工人阶级自身找到。首先,里昂工人尚未形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在斗争中,作坊师傅和帮工的要求不尽相同。赤贫的帮工在斗争中虽然最坚决、最英勇,但由于他们的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起领导作用的作坊师傅是手工业者,他们常常把帮工排斥在他们的组织之外。这就削弱了起义队伍的力量。
第二,互助社的主要宗旨是作坊师傅们在生产中相互支援,1831年起义中曾起过作用的罗讷志愿军是一个军事性质的爱国主义组织,除此之外,并无一个代表全体工人的组织。况且,上述两个组织在起义的高潮中均未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因此,就总体而言,两次起义都是缺乏组织的自发行动。
第三,1831年起义中,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外,工人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1834年起义中虽提出了为共和而战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并不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斗争纲领。马克思曾指出:“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①这正说明里昂起义工人尚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因而也不可能提出反映这个历史使命的政治纲领。
第四,里昂工人既不认识国家的阶级本质,也缺乏与反动政府直接对抗的经验,因而在1831年的起义中,在胜利的时刻,依然听命于政府官吏,以致起义胜利了却收不到革命的效果。这些说明了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是无产阶级武装反对压迫的尝试,斗争尚处在自发和早期的阶段。里昂的起义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去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尝试需待40年后的巴黎公社起义者们去进行。
起义失败了,但斗争教育了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不能对资产阶级政府寄托任何希望;而要有效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必须组织起来,加强团结,不仅为经济目标,也为政治目标而斗争。
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工人举行了支持里昂工人的示威。一些地方的农民受里昂工人的鼓舞,奋起抗税。伦敦和维也纳的交易所中证券价格因里昂工人起义而下跌。英国报纸忧心忡忡,担心曼彻斯特的工人可能会学习里昂工人的榜样。
里昂工人起义使法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资产阶级报纸惊呼:“我们这个商业和工业社会,如同一切社会,也有它的隐患,那就是工人。有工厂就有工人,随着工人日益众多和贫困,社会永无安宁之日。”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此时已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迈开步伐去登上欧洲的政治舞台。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1页。
① 该社成立于1830年2月30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政治团体,以反对七月王朝为宗旨,其成员写作印发过一些小册子,在工人中有一定影响。1833年10月改组为“人权社”。
① 法国古尺名,每欧那合1.188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23卷,第17页。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相关参考
世界近代史··里昂工人起义法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中的两次起义。1831年10月,里昂6000多织工为增加工资举行斗争。他们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于11月21日转为起义,一度控制全城
1927年火十字团成立火十字团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最大的法西斯组织。20年代下半期,随着经济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加上德、意两国法西斯的影响,法国国内开始出现法西斯组织。1927年,火十字团正
法国1848年革命19世纪40年代后期,法国工农业下降,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反对派以“宴会”形式举办的政治性集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基佐政府两次禁止预定于1848年1月和2月举行
1.18世纪到19世纪发生的欧洲历史事件18世纪处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中间,俄罗斯正步入自己的黄金年代,法国革命的热潮汹涌澎湃,波拿马拿破仑开始展露头角。这段时间欧洲最主要的战争是俄罗斯打败瑞典,
十九世纪德国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①。德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比较深入地完成产业革命,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本世纪初,德国超过法国,赶上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
一、专业的优势不一样。1、里昂三大由法学院、商学院、外语系、人文系、哲学系和一个大学协会组成,尤其以人文和社会科学见长2、里昂二大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科学为主,教学质量非常出色。3、里昂一大
20世纪20年代,法国经济一反19世纪晚期以来长期相对落后之常态,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飞跃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法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20年代法国经济之所以获得飞跃发展,主要得
路易十三是波旁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的长子,1601年出生,母亲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公国的玛丽·德·美第奇公主。他的父亲崛起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法国宗教战争,因此登基时贵族势力衰弱。亨利四世出身于新教贵族家
法国一考古学家团队对外宣布,成功于在位于中部勃艮第大区的一处修道院,挖掘出一大批超过800年历史的中世纪宝藏,当中包括不少金银珠宝。 据悉,法国里昂大学的学古学家团队
法国一考古学家团队对外宣布,成功于在位于中部勃艮第大区的一处修道院,挖掘出一大批超过800年历史的中世纪宝藏,当中包括不少金银珠宝。 据悉,法国里昂大学的学古学家团队